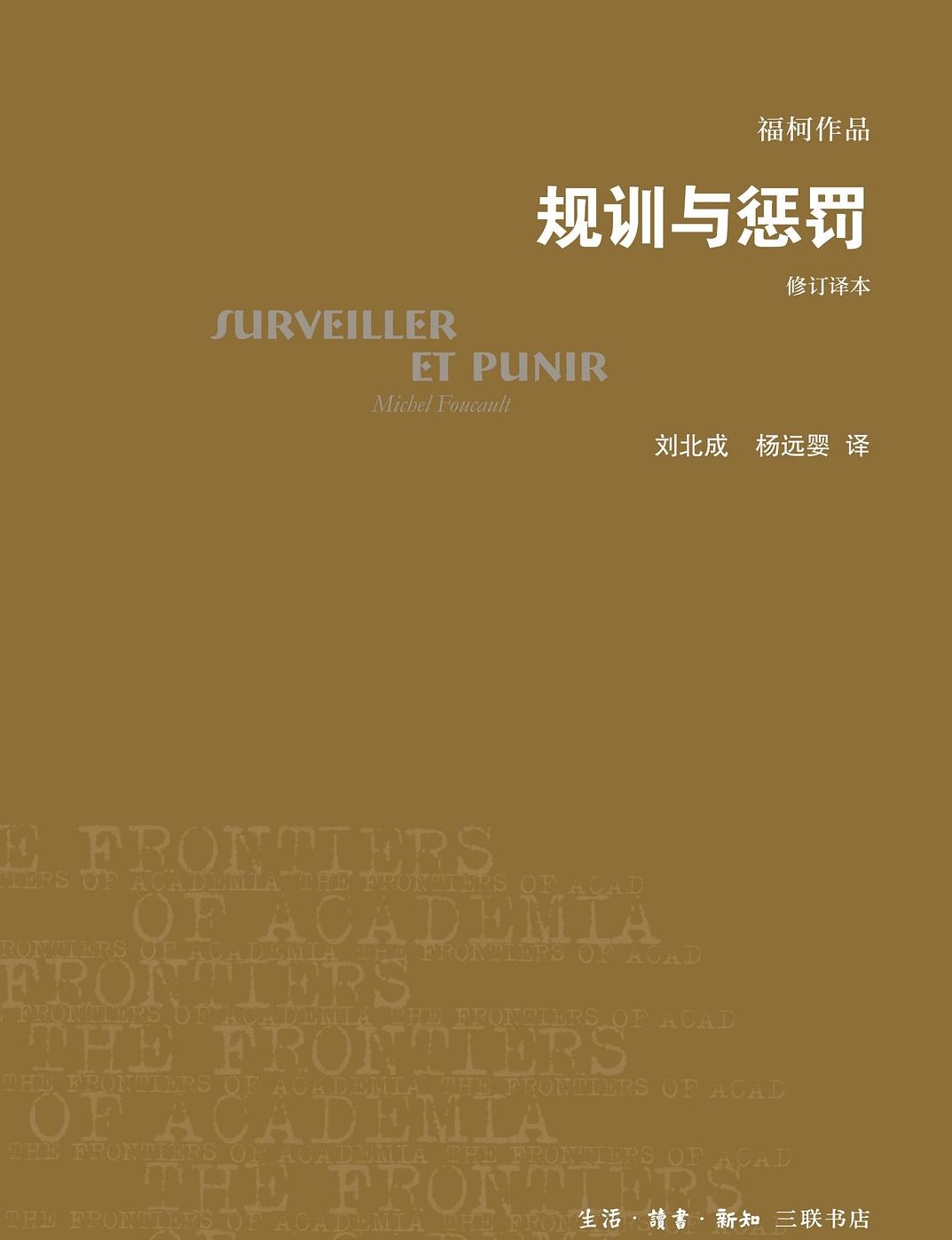
恰在读本书间,老球友约打球活动,因为群里有个律师女孩,无由聊起刑罚和辩护。群主说:
“对罪大恶极之人,要株连九族,你看看有没有威慑力。现在贪官污吏,牺牲他一个,幸福一家人,怎么能有威慑力?",“对连环杀人犯、人贩子之类,应该凌迟处死,贩毒让他吸毒慢慢折磨而死,让他们听说这个刑法都不敢犯罪,否则最多就吃一颗子弹,现在居然还有安乐死(注射死),这怎么能有威慑力!?”
云云。群主央企主管,学历不低。
在网上也常常看到网友建言应将某某用以大刑,以儆效尤。
可见,人们依然迷恋刑罚。而另一方面,刑罚又变得越来越温和。何以如此?
读了此书,豁然开朗。
此书开头讲述了18世纪法国一个残暴的刑罚故事,极具惊悚的画面感,相较于中国古代最严酷的刑罚,毫不逊色。
1787年,本杰明·鲁思(Ben-jaminRuth)在“促进政治研究会”上说:“我仅仅希望,在不远的将来,绞刑架、示众住、断头台、鞭答和裂尸刑轮这些刑罚史上的东西都被视为野蛮时代和野蛮国家的标记,理性和宗教对人们心灵影响微弱的证据”。
在刑罚史中,延长犯人极度痛苦的过程,尽可能让更多的人观摩刑罚的戏剧和恐怖性,是刑罚最重要的部分。福柯认为,惩罚要成为酷刑的话,必须符合三条基本标准:
- 首先,它必须制造出某种程度的痛苦,这种痛苦必须能够被精确地度量,至少能被计算、比较和划分等级。极刑是一种延续生命痛苦的艺术,它把人的生命分割成“上千次的死亡”,在生命停止之前,制造“最精细剧烈的痛苦”。
- 其次,酷刑应成为某种仪式的一部分。
- 第三,从规定酷刑的法律的角度看,公开的酷刑和死刑应该是引人注目的,应该让所有的人把它看成几乎是一场凯旋仪式。
19世纪初,肉体惩罚的大场面消失了,对肉体的酷刑也停止使用了,惩罚不再有戏剧性的痛苦表现。惩罚的节制时代开始了。到1830年一1840年间,用酷刑作为前奏的公开处决几乎完全销声匿迹。在本杰明说这话的60年后,范米南(VanMeenen)在布鲁塞尔宣布第二届教养大会开幕时,回忆起他的童年时代就好像在描述一个遥远的过去:
“我曾目睹过裂尸刑轮、绞刑柱、绞刑架、示众柱比比皆是的大地;我曾目睹过被刑轮车裂的可怕残骸”。
现代极刑普遍不再有血腥场面和恐怖示众的过程,甚至为了照顾最后一刻的感受,在即将行刑之际,犯人被注射镇静剂。这简直是一个司法保持克制的乌托邦:施加刑罚,但没有肉体痛苦。
何以如此?前述群主诉求的核心-惩戒恶人的示范效应-不再重要了吗?或者说最严厉的刑罚不再施加于肉体了?那么它又在哪里起作用了呢?
答案似乎就包含在问题之中:既然对象不再是肉体,那就必然是灵魂。
曾经降临在肉体的死亡应该被代之以深入灵魂、思想、意志和欲求的惩罚。
马布利“明确彻底地总结了这个原则:
“如果由我来施加惩罚的话,惩罚应该打击灵魂而非肉体”
福柯说:
这是一个重要的历史时刻。惩罚景观的旧伙伴——肉体和鲜血——隐退了。一个新角色戴着面具登上舞台。一种悲剧结束了,一种喜剧开演了。这是一种影子表演,只有声音,没有面孔,各种实体都是无形的。因此,惩罚司法的机制必须刺透这种无形的现实。
肉体上残酷的刑法,其作用是警示后来者。但人性对残暴的厌恶,又产生了两个对治理者来说十分糟糕的反作用。 其一,人们底层的善意,对这种做法有天然厌恶,总有一些不畏死的民众揭竿起来反抗;
“历史上自诩贤明之士的怪物发明和冷酷地使用了那么多可怕且无用的酷刑。有谁在读到这种历史时能够不毛骨悚然呢?”(Beccaria,87)。 “法律要我去接受对犯罪的最大惩罚,我怀着因此而产生的满腔愤慨去接受它。但是,实际上呢?他们却走得更远。……上帝啊,你让我们从内心厌恶给我们自己和给我们的人类>同胞制造痛苦,你创造的人是那么软弱和那么敏感,那些发明了如此野蛮,如此高超的酷刑的人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吗?”
其二,被刑罚的对象可能被人们塑造成英雄形象,而被追随。 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可见以死惧之并非上策。书中这样说:
罪与罚通过残暴联系和结合起来,这一事实并非某种被心照不宣地公认的报复法则的产物,而是某种权力机制在惩罚仪式中的效应。这种权力不仅毫不犹豫地直接施加于肉体上,而且还因自身的有形显现而得到赞颂和加强。这种权力表明自己是一种武装的权力,其维持秩序的功能并非与战争功能毫无关联。这种权力将法律和义务视为人身束缚,凡违反者均为犯罪,均应受到报复。凡不服从这种权力的行为就是敌对行为,就是造反的最初迹象,在原则上,无异于进入内战状态。
基于以上两点,上位者不再追求酷刑视觉效果和震慑作用,取而代之的是全方位的怀柔和教化,用规则引导,用训练教化。目的是让纪律内化。这合乎理性算计的结果,肉体摧残甚至消灭是双输局面。只有在肉体既具有生产能力又被驯服时,它才能变成一种有用的力量。这种征服状态不仅是通过暴力工具或意识形态造成的;它可以被计算,被组建,可以用理性设想出来。纪律discipline,在这里翻译成规训,书中规训和纪律并用,本质含义相同。
规训借助利益、表象和符号的理论,重构序列和发生过程,为统治权力的行使提供了一种通用的处方:权力以符号学为工具,把“精神”(头脑)当作可供铭写的物体表面;通过控制思想来征服肉体;把表象分析确定为肉体政治学的一个原则,这种政治学比酷刑和处决的仪式解剖学要有效得多。
在这种刑罚人道化的背后,是要求“仁慈”的原则,是一种精。或者叫惩罚权力经济学。
“愚蠢的暴君用铁链束缚他的奴隶,而真正的政治家则用奴隶自己的思想锁链更有力地约束他们。正是在这种稳健的理智基点上,他紧紧地把握着锁链的终端。这种联系是更牢固的,因为我们不知道它是用什么做成的,而且我们相信它是我们自愿的结果。绝望和时间能够销蚀钢铁的镣铐,但却无力破坏思想的习惯性结合,而只能使之变得更紧密。最坚固的帝国的不可动摇的基础就建立在大脑的软纤维组织上”
从肉体摧残到怀柔教导,彰显了人性的善意,显然是文明的进步。福柯借监狱和惩罚的历史来讲述这种"文明的进步”。在福柯看来是规训的全方位的发展,是理性算计和规划的结果。是工具和理论的综合协同的效果。
规训的重要工具,与刑罚结合的最好的方式,监狱设计的良好范式,即全景式敞视模式,是福柯规训的核心概念。全景式敞视最初是边沁提出的概念–在监狱的中心设有一个瞭望台,可以观察所有单独关闭的囚犯,而囚犯则无法窥视瞭望台的状况。这让观察者无处不在的影响被观察者,在最节省人力的情况下检验和巩固最良好规训效果,长期循环往复让被观察者行为约束内化并自动启动。
今天理想的刑罚目标应该是一种无限期的规训:一种无终止的审问,一种无限扩展乃至精细入微的调查,一种能够同时建立永不结束的卷宗的裁决,一种与冷酷好奇的检查交织在一起的精心计算的宽大刑罚,一种既不停地根据一种不可企及的规范测量差距又竭力促成无限逼近该规范的运动的程序。
全景式敞视模式即是一种无处不在的宽大刑场,它有无数的变体,学校、教会、培训机构、收容所、孤儿院……都能从它的变体中找到应用的场景。 规训在全景式模式下发挥最好的效用,规训的内容内化到对象身上,展开行动而不自知。规训和敞视不再是肉体痛苦的强力注入,人们接受灵魂的洗礼和被拯救,感受到心理按摩。人们不再抵触。谁会抵触爱,抵触被拯救,抵触为你好呢?即便抵触也没有着力点。
司法看着“平等”,法律机制看着“自治”,但包含着规训征服的一切不对称性。这让我想起马克思.韦伯的思考:韦伯认为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就是宗教仪式,病人就是教徒,治疗师就是牧师,病人的倾诉就是教徒的告解;病人和治疗师的角色权威性潜藏着不对称的关系,所以他们总能达成某种一致,就是诊疗师要传递的思想,方式就是诉诸不对称的权威,如同教徒忏悔后牧师以神之名义的宽恕。这是规训起作用的重要一面。
现代刑罚的所有重大的扩展变化——对罪行背后的罪犯的关注,对具有矫正、治疗和规范化作用的惩罚的关注,对被视为具有测量、评估、诊断、治疗和改造每个人的不同权力的权威的裁定行为的区分,所有这一切都表明规训检查渗透进司法审问。
人性对自然的向往,热力学自然熵增对无序的天然倾向,开始,人们一定会对试图建立某种秩序的规训有所不适。 就像植入人造器官的排异,就像“坏孩子”反对说教。 但当规训一旦完成,人们感受到的是,全方位的自由,又从不逾矩,一个脱胎换骨的新人,和一个真正的乌托邦。 这实在是一个大悖论。有点像斯德哥尔摩综合症。
规训的完成不会是一蹴而就,而是必定伴随着循环往复。孔子说的从心所欲不逾矩,说要到70岁。 到古稀才达到狗性内置的境界,看起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福柯实在比孔子看到更深一层,福柯提到现代刑罚不是要达到路不拾遗消灭罪犯的效果,而是制造大量的“过失罪犯” – 他们干的勾当无伤大雅。 “过失罪犯”很有用,是灰色地带的极好的平衡因素,被规训的“过失罪犯”是对抗黑暗的有利力量,是权力运作过程中受控的非法手段,是打入敌人内部的楔子。他们接受规训,依附权力,权力纵容他们。真正达到全局稳定和局部波澜的辩证统一。
亦喜亦悲?现代性是否昭示着,福柯所描绘的是一幅永无出路的”封闭盒子“的图景?自由只是被规训后自我催眠的幻象?
我看倒也不见得。正如福柯曾强调的:
每一个历史阶段都将逐渐逝去,其原因往往在于,它无法控制来自底层和劳动阶层的大众的反抗。如果说,规训在今天依然能保持高效,那仅仅是因为它还没有遭受充分的挑战,它之所以依然如此高效,是因它是以一种几乎“不可见”的方式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作用。
福柯自始至终用一种发展的历史观点来剖析,他不曾认定一个铁板一块的社会,也从未暗示左派的政治行动主义毫无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