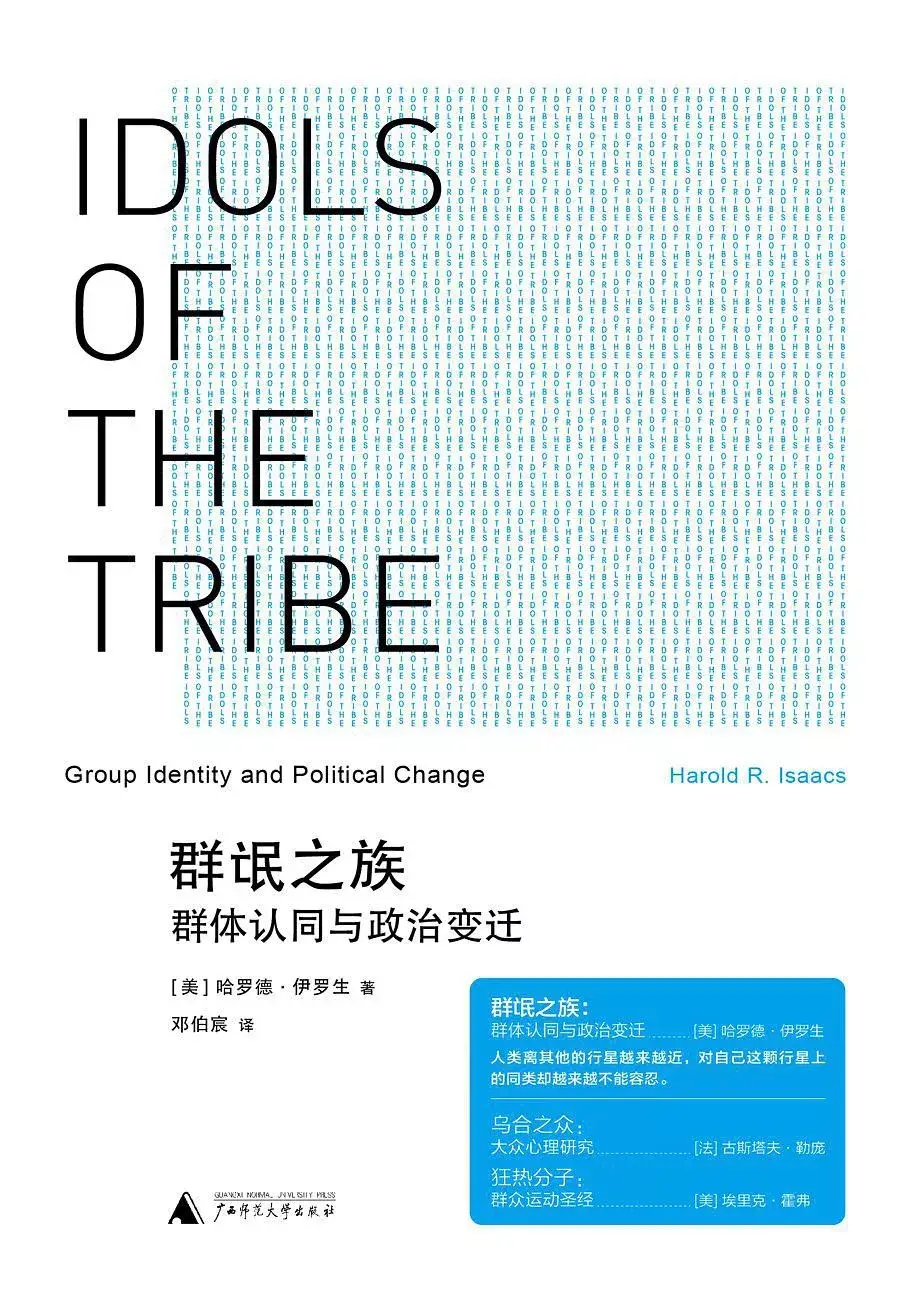
1
哈罗德·伊萨克斯这本《群氓之族》,写于1975年,站在战后世界秩序重构的节点,作者试图回答一个在当代愈发尖锐的问题:
为什么群体认同如此强大,以至于它能召唤战争?
书中所指的“族群”,不仅仅是血缘意义上的种族,更泛指一切能够形成心理归属、划分敌我边界的群体认同结构——从语言、宗教、肤色,到历史记忆、共同伤痕。
从苏联解体、印巴冲突、中东火药桶、恐袭频发,到卢旺达种族灭绝、黑人与犹太关系中的断裂与张力,这些血的历史无一不与“我们是谁”这个问题紧密相连。书中“姆庇之家”的概念象征了这种原始而本能的归属冲动:人必须属于某个“我们”,否则就无所依附。而这一归属 —— 起于激情,终于战争。
2
不管如何自由开放,群体认同的底层逻辑还是无处不在影响,人既怕不同而被落单,又时常处处彰显与众不同以突出群体的优越性。 一个国家的历史既是一种开来的力量,也可能是一种阻力,甚至诅咒。国家或民族都在寻找历史的遗迹,来加持前进中精神力量,这种力量往往比我们认为的强大的多。如犹太人,几经灭绝,这点香火也就靠两千年前的精神传续,这种精神/宗教传统是犹太人的“姆庇之家”,笃信他们是上帝的天选之人,让民族能够形散神聚。
菲律宾人则是反面例子,菲律宾历史基本上是被征战和征战后的屈服,美国人来了就依附美国人,西班牙人来了就归顺西班牙,又被日本人蹂躏。美国人和西班牙人比菲律宾人更高贵,混血的也要高其土著菲律宾人一等,这以然成为文化,奴性深重。菲律宾人也逐渐反思这种文化。问题是菲律宾从历史的蛛丝马迹中鲜能找到让他们沸腾的抗争事迹。苦难中抗争是一笔巨大财富,尤其是对一个民族。当一些菲律宾志士想要去追索他们的历史时,他们发现其实他们一向看不上的土著马来人--他们的同宗同源的同胞--才是血统纯粹的,他们未被美国人、西班牙人、华人、日本人混血。
3
土耳其的也很有意思,国人称“国中土耳其,……”。20世纪初,土耳其民族主义抬头,为复兴古老的土耳其,努力去寻找一个早于伊斯兰,早于奥斯曼,早于波斯人的古土耳其。1935年,土耳其名族主义领袖凯末尔,制造了一出戏码:在中亚某处,一个土耳其人站在文明的曙光中,面对太阳,吐出了人类第一个土耳其语的“光”,于是文明、语言从此诞生,从这个源头衍生开来俄罗斯、欧洲、中国、阿拉伯文明……。凯末尔国父的确很猛,不是玩笑,内外都能摆平,现在土耳其那些领袖没得比,包括现在左右摇摆搞平衡\暗地里与穆兄会眉来眼去的的埃尔多安。
到中国,文明是货真价实,汉文化源头从未中断,犹太人也是,以色列人可以讲者希伯来语,精神源头从未间断,不同的是犹太人是形散的,中国是形聚的,中国是向内的,汉文化像尊熔炉,总把其他入侵文化打散揉碎消化吸收消遁于无形。以色列人深刻认同自己犹太人身份,而又来自世界,犹太教底色上的多元,也是以色列复国后迅速崛起的原因。中国向内的文化传统,向来以中心和文化的俯视者自居的,容易有意识的忽视优质多元文化,开放性不够。文明的厚度是财富也是包袱。自信不盲从,更不自大。
4
宗教是对超验的信仰,是人对不确定性的恐惧寻找的心灵的庇护,按此说,宗教绝对是私人的。但我们看宗教史,结论却是: 宗教绝对不是私人的。虽说从马丁路德改革,宗教总体上更偏向个人了,但组织性无处不在。
何以如此?宗教是一种手段借此区分族群,群体能够增加个体间的心理连接,这种连接可排遣个体的孤独无力感,连接形成了力量,因此,宗教不但是安慰的活水,也是形成权力的手段。宗教间的摩擦冲突从来没见间断,而究冲突的本源,宗教信仰中义理本身并不必定是最重要原因,常常宗教只是方便区分敌我的标签。